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类此前在对流感的作战中屡战屡败?因为流感没有政府。
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到今日肆虐全球的H1N1流感病毒,在两者间将近百年的时间里,人类引爆了原子弹,把阿姆斯特朗送上了月球,在阿尔卑斯山的地底安装了电子对撞机,但却对流感病毒无计可施。
每次流感袭来,人类都充满了无助与恐惧,也渐渐开始了谨慎的防疫探索与实验。

在1918年9月,大流感第二波来袭,费城成为重灾区。相对于第一次遭遇流感时的茫然无知,人们已经有了少许的“防疫经验”。
1918年9月18日,费城卫生官员们开始与在公共场所咳嗽、随地吐痰和擤鼻涕的举动作战。口罩是必备之物,没戴口罩就别想上公交车。据说在美国旧金山,一名卫生官员竟开枪打死了一个不愿意戴口罩的男子。一夜之间,保持安全距离与卫生习惯成了所有人的《圣经》。有些宣传标语甚至写道:“吐痰等于死亡!”一天里竟有60人因为随地吐痰而被逮捕。
隔离制度与人体试验,也在此时派上了用场。波士顿的一艘兵船发生了流感,患者被送往切尔西海军医院。那里的罗西瑙上校与沃恩等医学家一起讨论了如何预防和控制流行病。罗西瑙立即将这些水手隔离,并且追查这些病人曾经接触过的人,将他们也统统隔离。几周后,罗西瑙开始在来自海军的志愿者身上进行病毒试验,这是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人体试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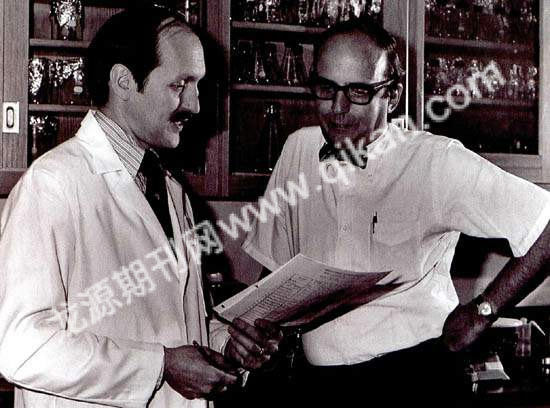
而费城的报纸,在此后不久充当了一次极不光彩的角色。9月28日,费城将举行一场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尽管卫生局建议取消游行,但报纸只字不提,或许是害怕丢掉一个新闻和游行时的华丽照片。但不久,更大的新闻就来了:游行结束后的72小时内,全城31家医院里的病床全部爆满。
在夺去了近2000万人(最高的估算达到1亿)的生命之后,流感自己销声匿迹了。但最早进行研究的保罗•刘易斯却也死在病毒手里。1929年,刘易斯奔赴巴西研究黄热病,却不慎染病而亡。但有人认为那是他怀才不遇后的自杀,而非病毒之过。
但有一个叫科恩•肖普的年轻人没有忘记刘易斯,还把刘易斯列为他论文的主要作者。而在1932年,正是这个年轻人发现从生病的家猪鼻孔里取出分泌物涂在其他动物口腔里,可以使它们染病。
第二年,英国科学家小组成功分离出了流感病毒。不久之后,肖普发现,出生于上次流感时期的人对“猪病毒”具有抗体,但1920年之后出生的人则没有。于是,他的结论是,横扫世界的大流感是由猪型流感病毒引发的,这种病毒本是由人传给了猪,但在猪身上潜伏了下来,又反扑向人类。
猪流感,由此得名。
1950年冬,爱荷华州大学病毒专家约翰•胡尔廷带着一支小分队远征阿拉斯加。他们找到了四具在冷冻状态下保存完好的尸体,在每对肺叶上取了5厘米见方的样本带回美国的实验室。样本上有被冷藏了几十年的流感病毒,但他并未能提取出活体病毒。
正当人们快要淡忘猪流感之时,流感抗争史上的另一个“大兵刘易斯”出场了。
瘟疫又现军营
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举国欢庆之时,无人察觉危险正在逼近,直到一个大兵的死。
1月,新泽西州迪克斯堡军营里,18岁的列兵戴维•刘易斯倒下了,被送到基地医院不久后死亡。他在几天前出现了流感的症状,但仍然坚持背着50磅重的背包参加了冬夜行军。
结果,这个大兵的执拗导致了科学们将近20年的困惑:刘易斯到底是因感染了“杀人流感”而病倒,还是普通感冒后的负重行军干掉了他?历史没有给出答案,但军营医疗主任约瑟夫•巴特利倾向于前一种结论,因为他发现1月底有300名新兵住院或被隔离。
新泽西的科学家小组对比了1932年的肖普猪流感标本与迪克斯堡新兵喉液样本,他们获得了惊人的发现,两者都是H1(血凝素1)N1(酸苷酶1)病毒!美国的医学界开始倾向于认为,1918年的恐怖流感通过动物繁殖存活至1976年,杀死了大兵刘易斯。当听到疾病控制中心的多德尔说“分离出的是猪流感病毒”时,美国武装部队军医研究负责人拉塞尔将军吓得张大了嘴巴。
那么,谁接触了猪呢?
专家盘查了迪克斯堡的新兵,发现22人的生活环境与猪有关,但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未患病。这让人们想起了2年前,明尼苏达一名16岁的男孩的死因极似猪流感。1975年,威斯康星州的8岁男孩患猪流感但最终康复。但没有人受到他们的感染,于是这两个与“疑似猪流感”的农庄男孩被人们遗忘了。
2月14日,疾病控制中心在其周刊上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猪流感通知:小规模爆发,死一人,“与猪流感相似”。
但调查并没有结束,疾病控制中心在迪克斯堡进行了大规模的血检,发现200余人对猪流感有抗体,13人曾感染过。3月13日,疾病控制中心的“猪流感特别备忘录”送抵国会,这份报告称,迪克斯堡流感与1918大流感有关;每个不满50岁的美国人都可能染病;大流感大约每隔10年发生一次。
1976年3月14日,美国政府进入了流感疫情防控紧急状态。
但至此,“猪流感”始终没有超越出迪克斯堡的地理范围,可是1918年大流感时的惨象还是让科学家们夜不能寐,预言者的使命感迫使他们要喊出“猪流感”这三个字。但第一个抓住“猪流感”这个历史机遇的并不是民众,而是四处寻觅危机的政治家们。
政治家掌管下的猪流感与民众性命

接种计划失败之后,胳膊上挨针的福特总统也在后来的大选中败给了卡特。失败的还有医学专家,他们预料的一场如西班牙大流感般的1976年流感并没暴发。1980年,《纽约时报》称,美国销毁了废弃的价值4900万美元的流感疫苗。这段“疫苗比流感杀人还多”的历史,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疫苗的看法。截至1993年,美国政府向猪流感疫苗索赔者赔款共9300万美元,都是纳税人的钱。
所以,2009年墨西哥猪流感爆发之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米切尔•里维特又把1978年出版的旧书《猪流感决策:一种难以琢磨的疾病》翻了出来,推荐给内阁成员阅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客在对待此次猪流感之时为何表现得缺乏作为,冷面以对。
当一次次瘟疫被当成是战争、政治与利润的工具之时,我们还将用什么来对付今日在全球横行无忌的猪流感呢?
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到今日肆虐全球的H1N1流感病毒,在两者间将近百年的时间里,人类引爆了原子弹,把阿姆斯特朗送上了月球,在阿尔卑斯山的地底安装了电子对撞机,但却对流感病毒无计可施。
每次流感袭来,人类都充满了无助与恐惧,也渐渐开始了谨慎的防疫探索与实验。

在1918年9月,大流感第二波来袭,费城成为重灾区。相对于第一次遭遇流感时的茫然无知,人们已经有了少许的“防疫经验”。
1918年9月18日,费城卫生官员们开始与在公共场所咳嗽、随地吐痰和擤鼻涕的举动作战。口罩是必备之物,没戴口罩就别想上公交车。据说在美国旧金山,一名卫生官员竟开枪打死了一个不愿意戴口罩的男子。一夜之间,保持安全距离与卫生习惯成了所有人的《圣经》。有些宣传标语甚至写道:“吐痰等于死亡!”一天里竟有60人因为随地吐痰而被逮捕。
隔离制度与人体试验,也在此时派上了用场。波士顿的一艘兵船发生了流感,患者被送往切尔西海军医院。那里的罗西瑙上校与沃恩等医学家一起讨论了如何预防和控制流行病。罗西瑙立即将这些水手隔离,并且追查这些病人曾经接触过的人,将他们也统统隔离。几周后,罗西瑙开始在来自海军的志愿者身上进行病毒试验,这是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人体试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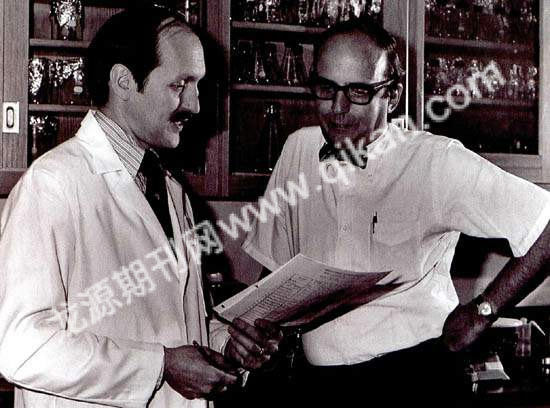
而费城的报纸,在此后不久充当了一次极不光彩的角色。9月28日,费城将举行一场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尽管卫生局建议取消游行,但报纸只字不提,或许是害怕丢掉一个新闻和游行时的华丽照片。但不久,更大的新闻就来了:游行结束后的72小时内,全城31家医院里的病床全部爆满。
在夺去了近2000万人(最高的估算达到1亿)的生命之后,流感自己销声匿迹了。但最早进行研究的保罗•刘易斯却也死在病毒手里。1929年,刘易斯奔赴巴西研究黄热病,却不慎染病而亡。但有人认为那是他怀才不遇后的自杀,而非病毒之过。
但有一个叫科恩•肖普的年轻人没有忘记刘易斯,还把刘易斯列为他论文的主要作者。而在1932年,正是这个年轻人发现从生病的家猪鼻孔里取出分泌物涂在其他动物口腔里,可以使它们染病。
第二年,英国科学家小组成功分离出了流感病毒。不久之后,肖普发现,出生于上次流感时期的人对“猪病毒”具有抗体,但1920年之后出生的人则没有。于是,他的结论是,横扫世界的大流感是由猪型流感病毒引发的,这种病毒本是由人传给了猪,但在猪身上潜伏了下来,又反扑向人类。
猪流感,由此得名。
1950年冬,爱荷华州大学病毒专家约翰•胡尔廷带着一支小分队远征阿拉斯加。他们找到了四具在冷冻状态下保存完好的尸体,在每对肺叶上取了5厘米见方的样本带回美国的实验室。样本上有被冷藏了几十年的流感病毒,但他并未能提取出活体病毒。
正当人们快要淡忘猪流感之时,流感抗争史上的另一个“大兵刘易斯”出场了。
瘟疫又现军营
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举国欢庆之时,无人察觉危险正在逼近,直到一个大兵的死。
1月,新泽西州迪克斯堡军营里,18岁的列兵戴维•刘易斯倒下了,被送到基地医院不久后死亡。他在几天前出现了流感的症状,但仍然坚持背着50磅重的背包参加了冬夜行军。
结果,这个大兵的执拗导致了科学们将近20年的困惑:刘易斯到底是因感染了“杀人流感”而病倒,还是普通感冒后的负重行军干掉了他?历史没有给出答案,但军营医疗主任约瑟夫•巴特利倾向于前一种结论,因为他发现1月底有300名新兵住院或被隔离。
新泽西的科学家小组对比了1932年的肖普猪流感标本与迪克斯堡新兵喉液样本,他们获得了惊人的发现,两者都是H1(血凝素1)N1(酸苷酶1)病毒!美国的医学界开始倾向于认为,1918年的恐怖流感通过动物繁殖存活至1976年,杀死了大兵刘易斯。当听到疾病控制中心的多德尔说“分离出的是猪流感病毒”时,美国武装部队军医研究负责人拉塞尔将军吓得张大了嘴巴。
那么,谁接触了猪呢?
专家盘查了迪克斯堡的新兵,发现22人的生活环境与猪有关,但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未患病。这让人们想起了2年前,明尼苏达一名16岁的男孩的死因极似猪流感。1975年,威斯康星州的8岁男孩患猪流感但最终康复。但没有人受到他们的感染,于是这两个与“疑似猪流感”的农庄男孩被人们遗忘了。
2月14日,疾病控制中心在其周刊上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猪流感通知:小规模爆发,死一人,“与猪流感相似”。
但调查并没有结束,疾病控制中心在迪克斯堡进行了大规模的血检,发现200余人对猪流感有抗体,13人曾感染过。3月13日,疾病控制中心的“猪流感特别备忘录”送抵国会,这份报告称,迪克斯堡流感与1918大流感有关;每个不满50岁的美国人都可能染病;大流感大约每隔10年发生一次。
1976年3月14日,美国政府进入了流感疫情防控紧急状态。
但至此,“猪流感”始终没有超越出迪克斯堡的地理范围,可是1918年大流感时的惨象还是让科学家们夜不能寐,预言者的使命感迫使他们要喊出“猪流感”这三个字。但第一个抓住“猪流感”这个历史机遇的并不是民众,而是四处寻觅危机的政治家们。
政治家掌管下的猪流感与民众性命

接种计划失败之后,胳膊上挨针的福特总统也在后来的大选中败给了卡特。失败的还有医学专家,他们预料的一场如西班牙大流感般的1976年流感并没暴发。1980年,《纽约时报》称,美国销毁了废弃的价值4900万美元的流感疫苗。这段“疫苗比流感杀人还多”的历史,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疫苗的看法。截至1993年,美国政府向猪流感疫苗索赔者赔款共9300万美元,都是纳税人的钱。
所以,2009年墨西哥猪流感爆发之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米切尔•里维特又把1978年出版的旧书《猪流感决策:一种难以琢磨的疾病》翻了出来,推荐给内阁成员阅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客在对待此次猪流感之时为何表现得缺乏作为,冷面以对。
当一次次瘟疫被当成是战争、政治与利润的工具之时,我们还将用什么来对付今日在全球横行无忌的猪流感呢?